2021年9月17日星期五
《新清华》(代发刊词):为本学期完成各项工作计划而奋斗
《人民清华》发刊词
《政治学报》创刊辞
《历史政治学报》发刊词
《复旦大学政治学报》发刊辞
2021年9月15日星期三
《史学年报》发刊辞
《新女性》导言
《中流》献词
2021年8月26日星期四
《红楼》发刊词:写在“红楼”剪彩的日子
亲爱的读者!当您正怀着愉快的心情,跨入新的一年的时候,《红楼》,身披1957年第一天的万丈霞光,呈现在您的面前。当它映入您的眼帘时,您那颗日夜盼望着它的心,一定和我们一样激动!
红楼,对我们并不陌生——
红楼,矗立在万人景仰的北京城里,也矗立在我们年轻人的心中,红楼的眩目的光芒照在革命史里,也照在我们年轻人的心上!在那惊心动魄的“五四”时代,它的顶上燃起了第一只斗争的火炬;在那茫茫的黑夜里,它的东面的一个窗口,射出明亮的灯光,那里跳动着一颗热烈的伟大的心——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它的另一个窗口,站着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他把犀利的枪,投向了狡猾的敌人!……
红楼,它矗立在北京城里,也矗立在我们心中——当我们要创办这个文学刊物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了这个名字。
我们的刊物以红楼命名的百花园。我们的百花园,必将五色缤纷,万紫千红。红楼的光芒照在花园里,这红光告诉我们,要学习五四时代青年的革命精神,要大胆地干预生活,要勇于和善于建设、支持属于我们时代的、使我们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切;也勇于和善于揭发、批评阻挠我们前进的陈腐的一切!我们的《红楼》,要具有青年人的特点;不仅主要是青年人写,还要求着重写青年;不仅主要是学生写,还要求着重写学生。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它将发表不同风格的创作,担负起鼓励和发扬广大同学业余创作热情的任务,成为我们自己习作的园地。我们的花园,欢迎从任何地方寄来花种,只要它是真的花,有生命,我们这里,便有它生长的土壤。
《红楼》即将创刊的消息刚刚传出,就得到同志们热情的支持:有的寄来了祝贺信;有的对未来花园的管理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更有不少的朋友送来了各种各样的花种……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我们办好这花园的信心。显然,党、团、学校行政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关怀就是我们这花园繁荣兴盛的全部保证。在这,《红楼》剪彩的日子,我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亲爱的读者!当您走进“红楼”的时候,对这个看起来还比较单调的花园,一定和我们一样,感到不满足。因此,我们希望:当您走出花园时,除留下宝贵的意见外,还要写上:这花园是我的,我要做一名园丁。
亲爱的读者,愿您象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一样,来希望《红楼》吧。它会在这么多园丁的关怀下,日益繁荣、成长起来的!
红楼,古老的红楼,像它身边的松柏一样,万古长青!
《红楼》,年青的《红楼》,像我们青年人的生活一样,万紫千红!
让我们向着红楼,倾诉我们激动的心情;让我们向着红楼,唱出我们愉快的歌声!
1956.12.31日
出处:原载于1957年1月1日《红楼》创刊号,无署名。
附:编后记
虽然确是经过了“千呼万唤”,《红楼》毕竟算是出来了。编者和读者有同样的心情,为我们共同的综合性的文艺刊物的先睹者而得到优先的喜悦。
这一期发表了张烱同志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作者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描绘了两个中国同学和一个留学生在学习上的互相帮助和在生活中的互相关怀,生动地写出了这些年轻人之间可贵的友谊和爱。
《车上》是从李亚白同志一部中篇小说里选出来的一章。这部中篇写的是:一个多少有些骄妄的青年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后,经过现实生活的教育,党团组织和同学们的帮助,在思想上逐渐得到锻炼和提高的故事。《车上》只是小说的第一章,作者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离乡赴校途中的主人公。
《明天是正月二十三》,是康式昭同志的一篇自传体小说。作者从深切的生活感受出发,绘制了一幅朴素而感人的图景,描画出旧社会穷孩子悲苦童年的一个侧面。
诗歌在这一期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反映着目前学校创作活动中诗歌占优势的实际情况。
廖天一同学的《致伙伴》,描写了今天向科学进军道路上全体文化战士由于伟大任务而产生的激动、对于赢得胜利的信念,传达了他们斗志昂扬的心声。
情诗——青春的花朵,也在这一期占有一定的地位。
发表的几首古体诗歌,体现着向古典文学遗产学习的精神,是力图利用旧形式为新内容服务的尝试。本着“百花齐放”的原则,各种式样、各种风格的作品都将能在《红楼》找到自己着根的土壤。
显然,目前这一期还远谈不上“令人满意”。如果要从北京大学确有写作能力来衡量,应该说,这一期是“不满人意”的。这首先是由于我们筹备过程中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没有充分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写作力量。致使目前的刊物在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和总的质量的保证上都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计划的许多栏目不能不留作空白;我们没有精悍的短论、犀利的杂文、辛辣的小品、……在诗歌方面我们没有优美生动的叙事诗、尖锐深刻的讽刺诗……在其他文学样式方面更是提不起来。
但是,我们相信:如果同志都说:“一定要把《红楼》办好!”并且伸出手来栽培它、支持它,那末《红楼》就不可能办不好,《红楼》就不可能不是一期比一期更充实更美丽。
出处:原载于1957年1月1日《红楼》创刊号,无署名。
《红楼》简介:
《红楼》(不定期)于1957年1月1日创刊,是北京大学校团委会领导下,由学生自办的综合文艺性刊物。总共出版14期(包括5期增刊),跨1957年和1958年两个年度,其中1957年出版正刊5期,分别是创刊至第6期(5、6期是合刊1册)。1957年,在正刊《红楼》出版以外,还出版过4期《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特刊”,特刊单独编号。
《新评论》(代发刊词):编辑后记
2021年8月16日星期一
《论语》缘起
《今天》致讀者
歷史終於給了我們機會,使我們這代人能夠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聲出來,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處罰。我們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為歷史已經前進了。 馬克思指出:“ 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要求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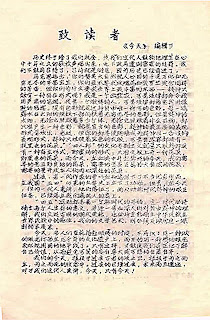
-
中国——一个一向被象征着“睡狮”的中国,现在显然已经不是什么怯懦、贫弱、守旧、无组织、不统一……等等代名词了!因为它已经站立起来;站立在暴风雨的大时代前,站立在被压迫者争取解放的高潮中。紧随着时代巨轮的转,她已将她所具有的一切人的、物的、有形的、无形的力量汇成一个奔腾...
-
我的《千秋評論》(李敖千秋評論叢書)辦了十年﹑《求是報》辦了半年﹐如今雙雙達成它們歷史的﹑階段性的使命﹐我決定創辦《李敖求是評論雜誌》﹐以開新猷。 《李敖求是評論雜誌》是我五十六歲時創辦的﹐由於我餘生生命貫注的主力是《北京法源寺》以外的幾部重要小說﹑以及非小說的《中國思想史》等書...
-
《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北京大学之生命已历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今日幸能脱弃旧型入于轨道。向者吾校作用虽日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























































